致逝去的年味散文
又是一年春來早,張燈結彩處處新。時光老人又把我拉拽到了這個時刻。在跌跌撞撞的日子里,那些被風化了的遙遠的記憶又重新被喚起。曾經消逝的年味如一杯醇香的老酒,沾在舌尖上讓人回味著無比的快感。——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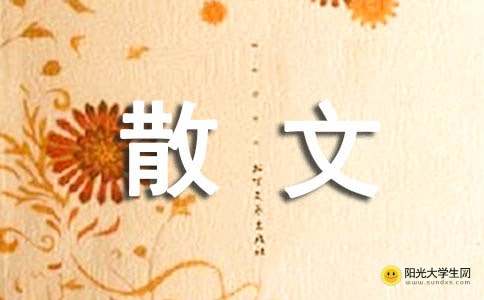
過了上七日,年味漸漸淡了。只是一些遠房親戚留到上七日之后,為了不中斷聯系流于形式的互拜一番,過年也算告一段落了。
“吃了元宵粑,各人尋東家”,這是過去討生活人的一句流行語,如今,往往等不到元宵,一過上七日,車站碼頭的各種交通工具上就人如潮涌,人們又紛紛踏上了外出謀生的征途。就為了這短短的年味,十幾天奔波于千里迢迢路的兩頭,怎一個“累”字了得?
過完年,我拖著滿身的疲憊又擠身于千萬打工者的隊伍行列之中。坐上列車還來不及好好安歇,我就又開始謀劃下一個春節了。隨著年齡的增大,過個年也總是覺得思慮重重,感慨萬千。每每臨近年關,藏在心底的思鄉之情被繁鎖的人情往來所代替的無奈,一個個沉甸甸的紅包,一桌桌豐盛的酒菜淡漠了當年的味道。感覺家鄉的年似乎是一個個人們相互攀比的賽富場。
過完年,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而今隨著節日的喜慶氣氛的慢慢褪去,身后的煙花迷霧的山村和醉意醺然的鄉親們都被長長的列車拋在了身后。有多少如我一樣的游子及他們的家人在體驗著骨肉分離的傷痛呢?
還是在年前十幾天左右,家鄉的父母就在細數著日子盼望著兒女們早早歸來,小孩子們站在村頭翹首企盼,離家一年的無論是兒女還是父母,都希望過一個團圓年。
平時冷冷清清的小鎮上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商店里早已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年貨,細長狹小的村道上一輛輛小車魚貫而入,突然變擁堵不堪。
在老家農村,最隆重的是在臘月廿七晚上或臘月廿八晚上的祭祖。歸家的人們無論如何都要在這個節點前趕到家,錯過了這個日期,過年對家鄉人來說也就失去了意義。現在人們忙于奔波,一大家子人能夠聚在一起過個年,再趕上全村的人都能在祖先祠堂里熱熱鬧鬧相互討個吉利,分個輩分大小,虔誠地祭拜一下祖先,那是一年中最奢侈的事了。
現在的年已經少了眾多可以記憶的環節。記憶中,小的時侯孩子們總是盼望過年的。過年了,有好東西吃,有新衣服穿,有鞭炮放。每年冬季一來臨,心中總會泛起一種憧憬的感覺,總在計算著時間的腳步。而那時的父母與我們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心境。記憶中他們總緊鎖眉頭,憂心重重,那種對于春節期間家庭的負擔的憂心是我們永遠無法體會的。
冬天一到,母親就開始為過年籌備。待到田里的蕎麥收割完畢,挑個晴朗的日子,父親就會從米缸里量出幾斗大米浸泡在水桶里,過兩、三個小時,母親與姐姐再把浸泡好的大米舀出攤放在家里的石磨上,一遍一遍把它們磨細成漿,第二天,就開始煎豆折了。
大人們在磨好的米漿里按比例參雜進蕎麥粉,用勺子舀起倒入鍋里干煎,兩口鍋同時進行,左邊鍋里剛倒入米漿,用一個大貝殼把它鋪張開來,蓋上鍋蓋,右邊鍋里的就熟了,剛起鍋的豆折就象面膜一樣又白又軟,然后放在木板上讓它冷卻,再卷成條,左鄰右舍的嬸嬸大嫂們也來幫忙,把豆折切成絲,曬干后留到年節時招待親戚客人食用。
煎好豆折后,家里又要準備熬制麥芽糖了。母親先稱好一、兩斤小麥,泡過水后放在陰涼處,等待它們發芽。往往這時候常會有制作爆米花的師傅上門,東家奶奶,西家大嬸紛紛從家里拿些大米來做爆米花。記得我母親很少要師傅打爆米花的,都是自己用上好的稻谷放在鍋里炒制,噼里啪啦米花在鍋里爆裂。母親常說家里炒的更好吃。那時的我經常扒著鍋沿,聞著母親一鏟一鏟翻出的清香。長大后才明白母親其實是省點加工費。等到麥芽長出來了,就開始熬糖了。麥芽糖一般是放在土灶上的大鐵鍋里熬制的,需一夜柴火不熄,專門有一個人拿鐵勺站在灶旁攪動。熬制過程費時費力,一般要兩個人偕同合作,輪番守護,一人累了再換另一人繼續。母親往往都是一個人熬制的。那時我們不懂事,只知道麥芽糖的美味。現在每每想起,那種甜而不膩,入口如絲綢樣柔滑細膩的味道時時刻在舌尖的味蕾上流過。熬制好的'麥芽糖加入爆米花后凝固成了香酥可口的爆米花糖,這也是春節招待客人的佳品。
那時,最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哪家養了一頭大肥豬,再賣點豬肉,過年就比較富裕了。宰好過年豬,那家女主人就會做一桌豐盛的殺豬飯招待屠夫,再叫上附近的親朋好友來慶祝一番。過年豬都要在立春前宰好,過了立春宰的豬,春節后肉品難以長久保存,所以每家每戶都會提前把豬宰好,留足自家過年吃的,剩下的就用鹽腌制,待到來年春耕時節再拿出來食用。記得我剛出門打工的那幾年,每臨近春節的時候,母親都會催促我早點回家,說別人家的年豬已經宰好了,咱家就等你回來殺豬啦。
臘月廿四送灶神,母親會提前把家里打掃的干干凈凈,在灶臺前點上一炷香,燒一令紙,擺放供品,在灶神面前說些好話,以免灶神上天在玉帝面前奏我們一本,導致來年家運不順。
記憶最深的是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說是有戶人家兒子生得相當聰慧,讀書過目不忘,算命先生說他有天子之命。送灶神那天,那家母親邊洗筷子邊哼歌曲,得意忘形之時,不小心手里的筷子在灶臺上敲了一下,這下可惹惱了灶神,灶神上天后在玉帝面前狠狠地奏了一本,“兒子還沒做皇帝,母親就這么驕橫無禮!不可用,一定要讓他脫胎換骨,貶為凡人。”突然間這個小孩骨頭嗞嗞作響,疼痛難忍,他母親知道惹了大禍,可已經來不及了,滿眼含淚地說:“兒呀,你咬緊牙根,立緊腳吧!”從此孩子的皇帝命是沒了,只留下了一嘴金口銀牙。傳說歸傳說,母親其實是借故事告訴我們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當然在年節前,家里還要做米糟,蒸年糕,磨豆腐等等很多鎖碎的事。在物質貧乏的年代,家家戶戶都是如此,為了過年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小孩子為了這其樂融融的年味,也跟在父母背后幫襯著。
臘月廿七,過年大戲也隨之正式拉開了帷幕。小孩們個個手提紅燈籠,這家出那家進。“嬸嬸,嫂嫂,年飯做好了嗎?”大人們都會笑臉相迎,會說,快了,快了!華盞初上,祖堂的神龕上一對大紅蠟燭把整個大廳照得通明,家家戶戶端來供品放在神臺上,點上香,燒好紙,此時祖堂的大廳上空煙霧繚繞,祖堂外鞭炮齊鳴。整個村莊都籠罩在一片喜慶祥和的氣氛中。祭祀歸來,就正式吃年夜飯了,望著香噴噴的豬頭肉,小孩們早已是垂涎欲滴,眼疾手快地爭著搶著。魚盤端上桌了,鴨肉上桌了……。一年中最幸福快樂的時光就定格在記憶里的這一刻。
大姐家是臘月廿八過年,錯開了時間,所以今晚大姐一家人也相聚我家,顯得更加熱鬧,更加融洽。此時此刻的父母坐在上席,看著子子孫孫圍成一桌,臉上綻放著幸福的笑容。親情,在這一刻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大年三十晚上,叫守歲夜。孩子們會到山上砍來木柴放在祖堂的大廳里,再從各家各戶拿干柴作引火,俗稱“歲火”。大人小孩圍成一團,講故事或討論村里的大事。也只有在這一夜,村里人才似乎能好好地聚在一起,心平氣和地面對全村的現在和未來各抒己見。面對高高在上的祖宗牌位,那血脈相承的族親拋卻了往昔松散,疏離的心態又重新凝聚在一起。
大年初一凌晨一到,此起彼伏的鞭炮聲就會響徹在整個山村的上空。這就是所謂的開門大吉,慶祝新的一年的到來。
初一上午全村老少相聚祖堂拜族譜,送祝福,然后是看今年的哪個方向大利,就迎著那個方向全村人圍著村子繞三圈,預示往后的日子里出門順順當當,平平安安。
最熱鬧的是初二開始,有同族的人來送戲,不為錢財,不為吃喝,就圖個開心。什么踩高翹啦,獅子滾繡球了等等好多節目都讓人們大飽眼福。你方唱罷我登臺,送走一批又來一群,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整個山村呈現在一派喜氣洋溢的氛圍中。
如今,這樣的場面再也不復存在了。
手機和電腦早已替代了原來最淳樸的民風民樂,紅包可以在微信上發,吃得喝得全可以在超市打包。即使年夜飯也可以由飯店做好送上門來。過去的年味與我們漸行漸遠,好多的傳統禮節都已刪繁就簡,只是鞭炮從原來的一小掛換成了幾萬響的大圓餅,夜空在焰火的照耀下五顏六色。小時候的紅燈籠早已派不上用場了。村子里四處燈光閃爍,煙花曼妙。
如今的過年已經流于一種形式了,望著堆砌滿桌的山珍海味,我卻感到索然無味。不知是我的味蕾變得麻木了,還是這些被人工催熟的菜肴早已失去了原汁原味呢?
大年初一早上醒來,妻子望著窗外驚呼,“怎么下霧了呀?”是啊!怎么下霧了呢?打開網絡,“春節霾”是出現最多的一個高頻詞。我們把天空妝點的瞬間美麗,然而色彩斑瀾之后,藍天不見了,清新的空氣遠遁了,留給我們的是灰蒙蒙一片。走在村頭巷尾:那紅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塑膠袋隨風起舞;塑料瓶,易拉罐在我們的腳下滾來滾去。年夜過后,山村的大街小巷一片狼藉。
過完了元宵,出行的人們拍拍屁股瀟灑離開,我們無奈地望著身后的山村,除了大肆揮霍和無節制消費,這個年還能讓我們記住什么?曾記得中央春晚上有個小品《讓環衛工人早點回家過年》,至今讓我記憶深刻。年味早已不是當年的年味,春節文化已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中被碾得模糊不清。
我懷念兒時的過年,懷念母親親手熬制的麥芽糖,懷念一群孩子們在鞭炮燃盡之后,去尋找剩下的小鞭炮;懷念村里的曬谷場上把載歌載舞的族人圍得里三層外三層的熱鬧場景……。那些都只能存在于我的記憶中了,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春節自然而然地添加進了新的元素,只是在創新的同時是否還記得源遠流長的傳統,是否顧及我們的下一代,讓天空變得更藍些,讓環境變得更干凈些?
我懷念兒時的年味,在年味中體會歲月的四季變換,感恩父母一年中為子女們的辛勤付出。現在的年味,我真不知道帶給子女的是什么?或許是我多慮了吧,下一代自有下一代的想法。除了無奈,我一樣在年味中沉淪,而背后,是我沉重的腳印!
雖說現在年齡大了,對年也沒有多少奢望了。只是在送走一年又一年的光陰,親眼看著它一次又一次跨過年的這道門檻時,不知道是傷感還是不舍,心里總會出現莫名的惆悵。
【致逝去的年味散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