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的村莊散文
院落、樹木、鳥雀,是村莊的物質構成,而歌唱,應該和裊裊炊煙一樣,是村莊存在的真正標志。從我的西北老家穿行而過,就會深刻地體會到,那些樸素的、真誠的聲音,就像空氣、雨露一樣,滋潤和豐富著村莊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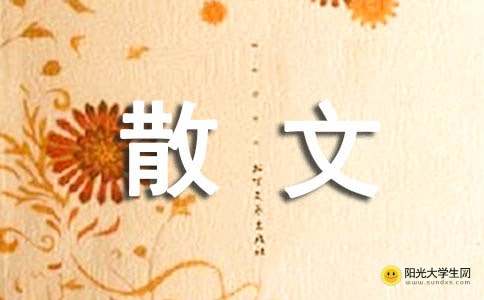
歌為心聲,不分四季。農歷三月,江南鳶飛草長、山青水秀時節,六盤山高一峰之下,才從春寒料峭中疾速走了出來,山野間的、村子里的桃花、杏花、梨花漸次開放,那粉的、白的、淡綠的色彩,霧一樣在村莊上空飄浮。這時,該辦廟會了。廟會是大型的祈福活動,按照習慣,唱社火是廟會活動中一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火,是社稷之火。鄉鄰們也習慣叫做野臺戲,或者大社火。之所以大,是因為要唱大戲。之所以叫野臺戲,是因為不在劇院一類的場所演出。社火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牽頭,一些愛熱鬧的鄉親參與操辦。三秦大地是公認的秦腔的發源地,陜甘寧的很多百姓都是聽著秦腔長大的。我的一位遠房小爺,因在陜西唱過幾年戲,相對于其他人來說,他在人物造型、臉譜等方面更具權威,經常被推舉為社火頭兒。小爺的戲唱得真的有板有眼,有一年,一位劇一團一的角兒聽見他唱《下河東》里的趙匡胤,就邀請他到劇一團一去,小爺舍不得幾畝莊稼,硬是沒去。有鄉親們抬舉,小爺的家就成了村子里排練社火的場所,他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指手劃腳的導演。十天半個月下來,《大登殿》、《轅門斬子》、《鍘美案》等本戲和《虎口緣》、《拾玉鐲》、《三娘教子》等折子戲竟然都能拿得出來了。這是鄉親們耳熟能詳的戲,但他們總是百看不厭。村子有小兩口,也是因為愛唱幾句才結成夫妻的。那年廟會上,女子在臺上悲悲凄凄唱《虎口緣》,他趴在臺口傻乎乎地看,她便記下了他。社火結束了,他又在戲臺后面張望,她就知道他在看她。廟會還沒有結束,他就打發媒人去提親。臘月里,他們兩家就成全了這樁喜事。鄉親們都說這是真正的“虎口緣”。
戲臺在廟宇的對面。臨時打成的大土臺子上,用胳膊粗的長椽扎起架子,再用篷布遮起來,然后掛上些花花綠綠的彩紙就行了。第一場戲,必定是手執鋼鞭的 “四大靈官”東打西打,說一些禳災接福的話,緊接著是“劉海撒金錢”,也說一些四季發財的吉祥話,接下來才演戲。十年前,村子里沒通上電,晚上演出全靠汽油燈照明,這家伙燃一燒起來半個世界都是通明的,可總在演到揪動人心的時候熄滅,急得臺上的沒有了激|情,臺下的也沒有了情緒。雖然如此,大家看戲的熱情不減,既便是黃風土霧天氣,也少有人回家。
我小時候看社火很有熱情,但從來沒有專心過。晚上,戲臺前還沒有一個人,甚至臺上的燈都沒有亮,就和幾個伙伴兒趴在臺口,等到開場,我們幾個已經是渾身塵土了。這個晚上是《火焰駒》,臺上的家當“哐哐才才”響起來,一個扮演武生的,搖著一根花哩胡哨的鞭子,做著趕馬的架勢,踏著臺步三扭兩擺地從后臺走了出來,我們知道他是誰扮的,就在臺口喊“一二一,一二一”,他就亂了臺步,跟不上鑼鼓的點子。這時,他故做鎮靜,搖著鞭子走到臺口,在我們幾個的頭上敲一下,我們得意了好多天。
廟會是有固定的活動時間、程式和內容的,而“花兒”則自一由得多。花兒分“河湟”和“涇水”兩大主系,我的老家一帶,是涇水花兒的傳唱地。一般不叫唱花兒或者喊花兒,而是叫做漫花兒,這一個“漫”字,沒有經過哪位文學大師的推敲,卻用得十分妥帖,包括了對空間、時間、形式的自一由解釋。過去,多是趕腳夫為了提神驅乏漫幾句,現在,鄉親們在鋤田、收割、耕種、打碾的間隙,興之所至,就可以漫上一段。有一位姓王的大叔,個子低低的,臉膛黑黑的,大概五十多歲,是村子里公認的“花兒王”。那年,應該是村子里最后一次集體打碾吧——隨后就實行了承包責任制。趁歇緩的空兒,男男一女女卻都喜歡往他那兒湊,你一言我一語,動員王大叔漫一板。“給咱來一板。”“漫個好聽的,打個乏氣。”他總是謙遜著不肯。如果有誰給他敬上一鍋旱煙,他便會應允了。
“山里的野雞紅翎子,
不叫哥哥叫名字。
山里的野雞白脖子,
給妹打上對銀鐲子。
山里的`野雞紅冠子,
給妹打上對金簪子。
鐲子簪子妹不愛,
要和哥哥過上一輩子。”
他的聲音不是很高,平常那種,但漫得婉切、動情,并且字句清晰,誰都能聽得見、分得清,好象是天生的漫“花兒”的材料。他起調的時候,先低低地“嗨 ——哎——喲——”,繼而猛地一停,緊接著細雨一般灑開,好象是專門為抓人的心似的。王大叔一直獨身,平時也少言寡語,我曾經私下揣測,他的情感世界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浪漫故事呢?
“鴿子飛到溝垴里,
我和妹一子要好呢。
鴿子飛到溝畔里,
我想妹一子心亂呢。
鴿子落在牛角上, 上一頁123下一頁
拿妹一子的手我拖上。
把手拖上心舒坦,
噙上舌頭比蜜甜。”
他漫花的時候,有些男男一女女的嘴巴一張一合,跟著他的調子,小聲地哼著。剛唱完,有幾個男的把幾個婦女推搡著,叫給王大叔給個舌頭。有幾個婦女嘻笑著翻身跑了,有幾個婦女半真半假的要王大叔主動走過來,然后才給個舌頭。他看著大家這么高興的樣子,也傻傻地笑著。我朦朦朧朧覺得,愛“花兒”的人,是重感情的人,重感情的人,也是最誠信的人。
樸實安逸的山村里,能貫穿于一年四季的,還有勞動號子——夯歌。有戰天斗地的勞動場面,就會有夯歌。記得上小學的那一段時光里,我除了三心二意地讀書,就是去興修水平梯田的地方去聽大人們的夯歌。夯,是夯實地面用的工具,每只大約有三五百公斤重,一般用石頭鑿成,現在多用水泥做成,呈柱形,下大上小,外面有五六個穿繩索用的鐵環,頂部靠邊處有一個深洞,是裝木柄用的。勞動時,領夯的人握著木柄,起著號子領夯,扯著繩索的人則整齊地應和著,這樣一夯下去,就有山搖地動的感覺。在我的印象中,打夯是最能體現一團一結協作精神的一種勞動。
打夯雖然是力氣活,但要求很嚴格,必須是年輕力壯、心眼兒好的人。我的大叔,那時大概不到四十歲,常常被一抽一去領夯。一般,砸虛土時,用的是慢夯號子。他起個頭唱一句,大家“哎哎嗨夯呀”應和著。在極具節奏的夯起夯落的過程中,那些土地被夯實夯平。慢夯調子相對悠閑,只要配合好了,大家還可以邊勞動邊看一眼天上的白云和嘰嘰喳喳的麻雀。
“繩子要扯勻(哎哎嗨夯呀),
力量要集中(哎哎嗨夯呀)。
號子要調上(哎哎嗨夯呀),
夯花要套一上(哎哎嗨夯呀)。
說抬一起抬(哎哎嗨夯呀),
說落一搭落(哎哎嗨夯呀)。
夯是公道佬(哎哎嗨夯呀),
誰奸把誰搗(哎哎嗨夯呀)。”
有時,也用快夯調子,比如砸地邊。快夯調子節奏較快,緊張急促,調子沒有了慢夯的悠揚,應和聲也取掉了拖得長長的尾音,幾乎象說話一樣。勞動過程中,大家的眼睛都緊盯著一起一落的石夯,生怕它跑了似的。
“打一夯啊(嗨喲),
連一夯啊(嗨喲)。
向前走啊(嗨喲),
一條線啊(嗨喲)。
齊心干啊(嗨喲),
夯得實啊(嗨喲)。”
事實上,對于村莊來說,最熱鬧的歌唱是在正月里。在土地上忙碌了近一年的鄉親們,這一月才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假日。進入臘月,確切的說,到了“臘月八”,鄉親們就開始準備正月里的娛樂活動了。臘月初八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吃“糊心飯”——一種糊狀的叫作馓飯或攪一團一的飯,大多用蕎麥面做成,蘸上油潑蒜調成的湯汁,十分好吃。這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習慣,說是吃了糊心飯,人們明亮的心就變糊涂了,可以把莊稼、心事都放了下來,一門心思用在鬧正月上。
馬社火是最傳統和最古老的演出形式。這個源于游牧民族,衍生于秦腔,在馬背上演出的劇種,大西北華夏子孫的家譜翻過了一頁又一頁,但它仍然生生不息地在西北大地上瘋長著。這是一個只演不唱的劇種。根據戲劇人物,打上花臉,穿上服裝,拿上道具,騎在馬背上,做一個造型就行了。馬社火裝扮起來,先要在村子里的麥場上演練一兩天,馬蹄踢踢踏踏,馬鈴叮叮鐺鐺,鑼鼓鏗鏗鏘鏘,場面十分壯觀。我小的時候,過年最喜歡的事就是和哥哥站在家門口等著看馬社火。那排著長隊、威風八面的的馬隊走過來的時候,那種興奮在今天也是很難找出詞匯來形容的。
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象我們這些孩子,不懂裝懂,你一句他一言的,對戲中人物亂猜。旁邊的大人便會告訴我們,馬社火的意思不簡單啊,前面的靈官寓意平安吉祥,紅臉關公寓意忠誠一團一結。大人們還說,那個人物是《白蛇傳》中的“盜仙草”,那個是《金沙灘》中的楊家將,那個是《五典坡》中的薛平貴。馬社火,幾個人物就是一臺戲。演繹了人間萬年千年的人性精華,藝術地呈現著人類生生不息,乞平安求賜福的生活追求。
與馬社火相比,“地攤子”則算得上是最原生態的說唱藝術。我的那位遠房小爺,一邊張羅著排練馬社火,一邊準備迎接“地攤子”。地攤子相對于“戲”,因為唱的不是“腔”,是曲子、小調,因此就歸入雜耍一類。由于規模小,程式簡單,不需要戲臺,隨便找一塊地方就可以耍起來,深受鄉親們的歡迎。村子里因為忙著馬社火,搞不了,就請外村的來耍。耍“地攤子”的時間都在晚上,地點一般設在村子里擺放磚瓦用的瓦窯坪上,近兩畝大的地,平坦而開闊。下午三四點鐘,大人們拿著掃帚、鐵锨去打掃衛生,孩子們也來湊熱鬧,偶爾還從大人手中接過掃帚,胡亂劃拉幾下。天剛黑下來,鄉親們就迫不及待地打著鼓、敲著鈸,到村口迎接外村的地攤子。 上一頁123下一頁
地攤子沒有馬社火隊的那種龐大陣勢,小鑼小鼓的,都不太響。也不知從哪兒拾掇來了一把淘汰的軍號,聽見我們村子的迎接的鼓聲后,就“吱吱嗚嗚”吹了起來,聲音很脆、很響,箭一樣,富有沖擊力。其實,這種迎接的辦法源自遠古迎接軍隊凱旋歸來的儀式,那軍號聲,是在告知他們距離我們村的距離。我那時對軍號十分好奇,不就是繞了幾個圈兒的銅管嘛,怎么會發出聲音來呢?為此,幾個小伙伴們給號手大獻殷勤,一會兒端開水,一會兒找火柴點煙,才換得了可以拿過來摸一摸試試的機會。輪到我拿過軍號時,才知道這家伙沉甸甸地,有些分量。便鼓著腮幫子,努著嘴,掙得眼珠子都快出來了,可就是沒有吹響。
地攤子的行頭不多,各自的家當、服裝各自帶著,很是簡單。演員在來之前已經畫好妝了,他們到了瓦窯坪上,把寬大的戲服往身上一套,算是一切就序,只等著開場了。樂器一般是二胡、板胡和笛子,這些樂器看起來簡單,可一齊吹拉起來,曲子十分好聽。演之前,我那小爺在地上劃了一個大大的圓圈,就分出了演與看的界線。那根白天栽好的高高的桿子上,掛著兩三盞罩著玻璃的燈籠,點燃后,場子里一下子明亮了起來。孩子們總缺少耐心,還沒有開場,就竄來竄去的,惹得大人們煩,他們就揮著手說:“去去去,走遠點耍去。”真的走遠了,卻又碰上談情說愛的男一女,他們也說:“去去去,遠處耍去”。
開場時,有一個掛著一嘴胡須的,不知是什么人物,搖著一把羽扇,穿著一身藍袍,先在桌子上的香爐里燃起幾枝香后,說道:“頭戴素珠八寶妝,爭福爭壽免禍殃。香爐飄出三股煙,風調雨順太平年。”他每說一句,小鼓小鈸就“嚓嚓、嚓嚓”響幾下。接下來才正式演唱。場子中央的道具是一根一米高的樁子,樁子頂端座著個斗形的箱子,箱子四周罩著玻璃,也點著個燈,箱子的四個角子上還挑著一串用紙扎成的五顏六色的花。這個道具名字叫“花燈”,演出的節目叫《十五觀燈》。二胡、板胡先拉上一段曲子后,一男一女手里搖著折扇,扭著“十字”步,從圍觀的人群中走了出來。一問一答地唱道:
“正月十五燈花開,
叫一聲妹妹觀燈來。
觀了頭燈觀二燈,
盞盞彩燈觀分明。
一盞燈,什么燈?
月明路上呂洞賓。
……
十盞燈,什么燈?
王祥臥冰孝娘一親。”
他們邊唱邊圍著場子道具轉,就好象在某條繁華的街上美美地看了一會花燈,并且還能叫得上花燈的名堂。緊接著是合唱的曲子,七八個女娃娃,也搖著折扇,邊扭邊唱,聲音高過了器樂聲。“一唱祝英臺,鴛鴦戲水來。二唱祝英臺,蜜蜂采一花來。三唱祝英臺,梁山配英臺。”這個曲子叫《十唱祝英臺》,是鄉親們十分喜歡的情愛故事。她們低著頭認真地唱著,拉二胡、板胡的在每句后“幫腔”,唱“伊兒呀”或“伊呀伊兒喲”,使這簡單的曲子多了份動人的神韻。村子里的幾位行家,也跟著幫腔,樣子很是投入。地攤子一直會耍到十一二點鐘才罷。而鄉親們也就在這種虛擬的場景中享受著快樂,不知不覺中認可著曲子所演繹的故事。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這些源自鄉親們心底的聲音,是村莊的構成部分,是老家的交響樂。他們愛它,就像愛自己的孩子,他們對它所付出的,就象對土地所付出的。它很重要,是鄉親們的土地和糧食。
【歌唱的村莊散文】相關文章:
1.關于村莊的散文
2.目光里的村莊散文
3.我的村莊優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