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村瑣記散文
說到王村,在兒時的腦海里,那是與北京、上海一樣的大城市!能夠有機會去趟王村,特別是趕趟大集,回來都要幸福的好幾天睡不好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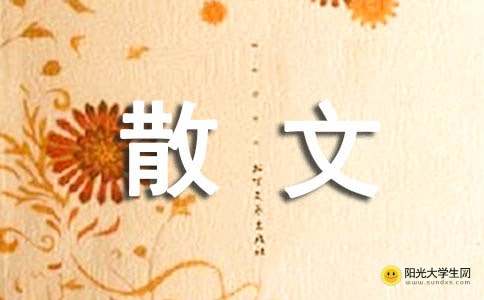
很久沒有到王村街里走走了,昨日回家返程,心血來潮,忍不住就走了進去。真是“相見不如懷念”,面目全非的一切,令人十分的傷感和失落,舊日的美好只能夢尋了。
王村,殷商時為姜姓諸侯國__逄國所在地;春秋至南北朝期間為“逄陵”邑(縣)治所;元至順元年(1330年),因王姓立村,地處山谷,故名王村峪;明代中期店鋪林立,又稱王村店;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為淄川縣正西鄉,簡稱王村
王村地處魯中,西鄰章丘普集鎮,東鄰鄒平臨池鄉,南倚泰沂山脈,北靠有泰山副岳之稱的長白山做天然屏障,歷來是商旅云集、人才輩出、富庶一方的魯中重鎮。
悠悠古鎮,幾千年來不知上演了多少傳奇。
小時候,讀語文課本中聊齋故事《種梨》,那故事中的情節常常讓我想到王村。我想在西埔村畢家當私塾先生的蒲老先生,離王村僅有一步之遙,一定無數次的來趕過王村大集,一定是在某年臘月的大集上,看到那些為富不仁的事情,才構思寫出的《種梨》!許多次,我在夢中夢到《種梨》的場景,就發生在釀制王村醋老作坊《井泉居》的對面。
老家西山南面東嶺山,又稱茶葉山、查牙山,《聊齋》有篇《查牙山洞》,其描寫惟妙惟肖,如果不是親臨探究那是很難寫的如此生動的,而要探究這查牙山洞,則是一定要過境王村的。
“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在西埔村生活了三十八年的蒲老先生,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一部《聊齋》笑看人生,而那書中描寫的大量故事,無數的語境,何止是《種梨》、《查牙山洞》,許多都能找到王村的痕跡。
王村,我兒時記憶最美的地方,我無限向往的地方啊……
王村最熱鬧的時光無疑是那逢陰歷二、七的大集了!尤其是每年春節前臘月里的大集,從北門到南門,從西面圩子墻到東門,大街上擠滿了賣土特產品和置辦年貨的鄉親。
趕王村大集,四鄰八鄉的鄉親,無論是賣東西還是買東西,都是三五成群結伴而行,一大早起床,披星戴月早早趕來。至于那推車挑擔來賣山貨的北山里的父老,更是天不亮就要起床收拾,摸黑徒步遠行,為的是早早趕到,能在集上占個有利的位置,讓東西賣個好價錢。
有一年臨近春節的一個大集,為了賣點自種的花生,換點錢過年,父母不到四點就起床忙活。父親拉著風箱燒火,母親不停的用鏟子在大鐵鍋里翻炒著,當滿滿的兩筐花生炒好的時候還不到五點。跟著父親翻過南山,走了一個多小時,天才擦亮。我想,這會我們一定能找個最好的位置,可到集上一看,最好的位置竟然早早有人占了。
王村周邊的集,一到中午就基本散的沒有人影了,唯獨這王村集是一直要熱鬧到下午四五點鐘的,遇上年集,不到掌燈時分,那集是一定散不了的。
小時候隨父母數次到過王村,大多是來趕集看熱鬧。
最初的一次應該是剛剛上小學,有一天聽老師講《鐵道游擊隊》的故事,迷上了火車,但山里那有什么火車啊!?一位大哥哥講,在北山頂可以看見火車。春天一個周末的早上,新雨過后,碧空如洗,我一口氣爬到了北山嶼子頂,站在高高的巨石上,等待著火車的出現。當火車從山口迅速閃過,長鳴的汽笛遠遠傳來的時候,我的心一下就飛到了王村,且從此念念不忘。
在我不停的糾纏下,那年五月櫻桃下來的季節,我跟著趕集賣櫻桃的父親第一次來到了王村。
一個上午我什么地方都沒去,就蹲在火車站看來往的火車了,當忙完的父親來叫我回家的時候,我仍然意猶未盡。
也許是我與王村有緣,也許是命中注定!數年之后,王村竟成了我人生重要的驛站。從當年背著簡陋的行李泰安求學,到濟南參加工作,回家看望父母。無數次來來回回,都要從王村穿行而過,每每都會自覺不自覺的停下來駐足片刻。
王村大集遠近聞名,不僅吸引著臨近的父老鄉親,就連桓臺、博興的鄉親都慕名而來。每年秋季,馬踏湖葦子成熟過后,當地農民都用葦子編成葦薄,用車運到王村大集,一卷一卷的豎靠在西門圩子墻上叫賣。
王村的圩子墻,是當年周邊村鎮最結實最宏偉的,兒時見到的.雖只剩西門附近的幾十米,但那高高厚厚用沙石和糯米漿壘成的圩子墻,依然堅硬如鐵,威風凜凜,黝黑斑駁的墻面處處透顯著當年的雄風。
四面八方到王村趕集的鄉親,一般都是沿著王村的東西大街,或擺攤叫賣、或來來回回選購自己喜愛的物件,就是閑逛看熱鬧的也大多是在這條大街上徘徊。
整個大街的熱鬧程度,比之《清明上河圖》上的街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從圩子墻旁的西門進入大街,剛走幾步就是北面的牲口市。牲口市一般是秋后農閑季節才有,四鄰八鄉大牲口的交易都在此。
當時,凡是來購買大牲口的鄉親,都是各村生產隊選出的熟悉牲口習性的能人,由于擔負著全村的重托,購買前,都要反復查看大牲口的牙口,以確認大牲口年齡和健康狀況,當看中后,買者和賣者就會在襖袖里手碰手比劃談價,而兩人面上的表情則是一反一正、陰晴不定,當兩人一起笑容滿面的時候,一宗生意已經是皆大歡喜。那情形既神秘,又好笑,實在令人難忘。
再往前走不遠,大概兩百米左右,斜東南就是街上有名的工農兵飯店了。黃色的“工農兵飯店”門匾醒目耀眼,匾上面是一等腰三角形的水泥墻,墻上頂端是一閃閃的紅星,下面則是“為人民服務”五個金色大字,讓人親切溫暖,很遠就能看到飯店的入口。現在想來,這個飯店還真是名副其實的為人民服務的工農兵飯店。
飯店里擺放的都是圓桌,出飯菜的窗口在靠東的南墻上,東墻根有一大的搪瓷保溫桶,免費為來吃飯的鄉親提供熱水。
來吃飯的多數都是趕集來賣東西,過了中午飯時的農民。有的人滿身塵土、一手老繭,有的則是滿臉汗水、一鞋的泥巴,但飯店的服務員從不嫌棄。
很多農民進來吃飯是不買飯菜的,都是坐在圓桌旁,倒一碗熱水,吃著自帶的干糧和咸菜,只有少數手頭寬裕的村民才偶爾買上一兩份便宜的菜吃。就是這樣,飯店的服務員也從來不趕村民,任由村民的性子,自由的進出。
記不清飯店都賣什么精美的菜肴了,只記得每次趕集,父親都到此來給我買兩個肉火燒,看著我狼吞虎咽的吃下,自己只花五分錢買一碗西紅柿或菠菜湯,就著自帶的煎餅填飽肚子。那香噴噴,咬一口滿嘴是油的肉火燒,現在想起來還直流口水。
沿著飯店繼續往東,很快就會看到路北一高高的平臺,平臺上是一高大的青磚院落,處處透著神秘,緊靠大街的南門,象極了過去的官府衙門或寺廟的大門,門口坐落著兩個威武的石獅子,拾級而上,踏入院內,一左一右兩顆粗大的柏樹直指藍天。
小時候這里是王村鎮醫院,家里小妹在這住院的時候去過幾次,但我怎么看都不象醫院。過后,問從小在王村街里長大的二姑,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記得那個地方老輩人叫大寺廟。我想叫什么和是什么已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片高大的建筑一定是大有來頭的!一定藏著許多神秘傳奇的故事吧!
緊鄰醫院東面,就是王村街里最有名的大灣了。圓圓的大灣周長有著七八百米的樣子,深有三十幾米。雨季來臨,大灣注滿雨水,趕集的鄉親圍著大灣,叫賣著自產的瓜果桃李、蔬菜水鮮、草柳竹籃,此起彼伏的叫賣聲,和著大灣里歡快的蛙鳴,就象一曲斯卡布羅集市奏鳴曲動聽悅耳!
大灣最輝煌的日子當屬年集的日子,那時,進入臘月,數九寒天,大灣里已經基本無水,即使有,也已經結了厚厚的冰,如此,這里就成了售賣鞭炮的最佳地點。
趕年集的人,多是青年男女,特別是最后一個年集。此時,家家戶戶的年貨大多已經置辦齊全,沒有置辦或置辦不全的就是那過年家家不能缺少的炮仗了!
來大灣賣炮仗的客商大多來自陽信、桓臺,往往一家占居一個區域,先是扯著嗓子大喊:什么泰山不是壘的,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賤賣了!賤賣了!我的炮仗最最響,瞎竄亂轉必上當等等五花八門!然后就是扯出幾掛炮仗或拿出幾個二踢腳、鉆天猴什么的點燃,用響聲吸引大家。各個攤位你方唱吧我登場,你來我往,此起彼伏,氣氛熱鬧到極點!此時,那沉不住氣沒有經驗的一些半大小子,往往紛紛掏錢購買,然后拿著炮仗開心的回家過年。而那些有經驗的老者,則不論你如何吆喝,只是遠遠觀看,就是不買。他們知道這炮仗年前不賣,年后就沒人要了!嘿嘿,下午的炮仗比上午可要便宜多了!
熱鬧非凡的炮仗市,經過一天的喧囂,在趕年集者幾乎人人開心滿足的抱著炮仗離去之后方才歸于平靜。
王村大街,有一個地方是不得不表的,那就是我兒時心中的圣地__大灣正東路北的新華書店。清晰記得,我的第一本新華字典是父親到王村供銷社收購站,賣了家里的兩桶土蜂蜂蜜,在這里購買的。
隨父母趕集,我從不買任何的東西,唯一的要求就是到書店看書,走時買一本喜歡的小畫書。《雞毛信》、《地道戰》、《盛習友》、《解文卿》等等都是在此選購的,以至到中學,我就攢下了一大木箱的小畫書。
成年后,一有空就想逛逛書店,我想,這習慣應該與當年有著一定的關系吧。
從書店再往東走,百貨商店、副食商店等林林總總,但那都不是我喜歡去的地方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每次趕集,都要去副食商店打點醬油,買幾瓶陳醋,趕年集更是如此,因為那天下首創的王村小米陳醋是過年打酥鍋最好的調料了……
說不盡的鄉愁,道不盡的情懷!鄉愁是一杯水,鄉愁是一碗酒!鄉愁是梧桐花下母親的嘮叨,鄉愁是彎彎山路上父親的萬般叮嚀!鄉愁是故鄉的裊裊炊煙!鄉愁是家鄉芬芳的泥土……
讓我們留住鄉愁!永記鄉愁吧!
【王村瑣記散文】相關文章:
1.京城瑣記的散文
2.望蓮瑣思散文
3.臺灣小吃瑣記隨筆
4.養蠶瑣記小學作文
5.高三瑣記隨筆
6.瑣記讀后感
7.圣誕瑣記初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