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土地經典散文
最近經常想關于土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因為突然從一個打工白領變成一個偏遠山鄉公務員的緣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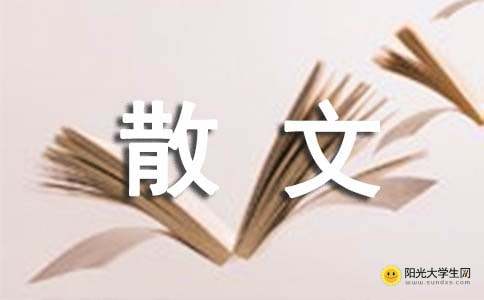
我到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錫鄉政府上班不久,便聽到過一句關于在大錫鄉種莊稼的笑話:“只要明星村的趙支書種什么,那你千萬別一樣,不然肯定把褲子都虧掉”。當時聽了付諸一笑,后面想一想,這句話實際上很能反映林區百姓特有的思維方式。我從小在農區長大,父輩們都是農民,家里田畝也較多,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開春播種插秧,夏季雙搶,秋收冬歇,年復一年種稻吃米,很少去思考“種什么好”的問題;而我工作的江華縣大錫鄉是最典型的林區,山多地少,大多時候都會通過流轉將土地集中起來經營,所以“種什么”,還真的需要考量。
那么種什么好呢?當一個問題到了很多人必須回答的時候,自然就升格為“話題”。有人熱議,有人到處取經借種,有人屁話不說直接捋起袖子干了。每每這種時候,我總是能感覺到一種力量在血脈里暗中流淌,在這些瑤山漢子微微彎曲的背脊和拼命鼓起的胳膊肌肉中,蟄伏著一個雷聲隆隆的春天。平日里抽著煙露出滿口黃牙憨笑的大哥大叔,菜市場上提著秤桿找電秤斤兩必爭的阿姨阿婆,在莊稼種下去的那一刻,都華麗麗變成了CEO。我至今都能很清晰地記得跟一個老農站在田埂上聊天的場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左手夾煙叉腰,右手指東畫西,吐著煙圈把隔壁老廖家的冬瓜西瓜貶得一文不值,把自己種的番薯茄子說得天花亂墜。那種自信,如同一個將軍握有獲勝的所有籌碼。
這些看似再平常不過,卻都是我所喜聞樂見的。我雖已從農村走出來,工作生活卻總也繞不開農村;一路來眼見的、耳聞的大多是不怎么開心的事情,包括風氣的腐變,人心之不古,以及那些日益陌生的少年“閏土”和一個個回不去的故鄉。所以當某個黃昏,我蹲在大錫鄉間田埂上,跟一位滿口黃牙的老農抽著煙聊著莊稼和土地,我傷逝的情懷便會有一種復蘇的的酥麻感,心里也會是滿滿的。
但我的心情依然是復雜的。土地之在我的世界觀,是一個帶有命運色彩的要素:一方面我看到了人性向上的力量,也算是再一次看到了追求幸福、永遠年輕的農民們;一方面我悲觀主義的思維慣性總讓我替他們擔心——種什么呢?在我看來無非是兩種:種下希望的同時,也種下了風險。人的力量在大多事情中都起著決定作用,但大多時候,“他人”往往決定著“己事”。這個以“市場”為標簽的時代里,瑤山漢子們在如何把握自己命運這個課題上,還需要交幾年學費。
去年中秋過后的某一天,我在明星村活動中心門前的小河邊,碰到了蹲在河岸上的趙支書。他獨自把煙抽成了煙屁股,見我來了,又分了煙接著抽起來,聊著就聊到了莊稼。
“價錢不好......”趙支書依舊是笑容不減,但言語間難掩苦澀。他種的是紫薯,收成很是不錯,但碰到了跳水行情。“明年出去打工算了......有個沙場,4000多一月,還帶買保險......”說到新年新打算,趙支書似乎又有了開春播種時那種揮斥方遒的風度。
但我只能陪著窮樂呵,安慰一個失落的老男人,我還不夠資格。在我的記憶中,大錫鄉這幾年的產業開發實驗中,無論是政府主導的還是農民自主的,大多都是成功至少是不虧的,但能夠清晰地在我腦海中留存再現的,卻往往是這些“把褲子虧掉”的例子。那年與趙支書有相同命運的還有龍安村的阿麗姐,還有新安村熊姐種的紫長茄也碰上了打霜天氣收獲不好。而他們都依隱樂觀微笑,常年在高山上勞作,讓他們有著一種特有的豁達氣質,他們自我嘲笑著,自我解構著,然后把一個個沉重的包袱都埋在土地里。那年的冬天,阿麗姐回了她闊別多年的湖北老家,很多人都說她會長時間呆在老家打工掙錢了;熊姐把熊姐夫打發去了廣西打工,自己在家陪著孩子上學,說安頓好了不定也隨了姐夫走;趙支書,坐在河岸上看著遠方獨自抽煙......
而我只能陪著樂呵,心里已經做好了來年在大錫鄉看不見這幾位的打算。從效益的角度來說,出去賣力氣掙錢跟把汗水灑在土地里區別不大,都是誠實勞動,都是養家糊口——人都喜歡把生活當成一張紙,正面寫壞了,就想試試背面,就這樣不停換著面,終究是離不開這張紙,但這個過程讓人釋放了壓力,邂逅了希望。
我當時以為這是最合理的解釋,也支持他們做這樣的選擇。但年后,當我從家鄉的春節回到春天的大錫,我卻又看到了嶄新歸來的阿麗姐,看到了不喝酒只臉紅的熊姐夫,看到了站在田埂上抽著煙寒磣隔壁老廖家西瓜地的趙支書。
聽說,他們今年打算種點別的......
我到大錫后,不知道為什么會經常想起我故去多年的外公,現在我算是明白了,在大錫這個群山環抱、綠樹人家自清涼的地方,依然有很多人,和外公一樣,跟土地有“過命的交情”。外公年輕時曾是鄉公所的一名中層干部,如果按照正常的軌跡發展,到現在我至少也能混上半個“官三代”。但在那個以“饑餓”為標簽的年代,他放棄了“公家人”的身份,回到了農村,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壯漢,聽說能挑200斤上陡坡,能將半截兒磚頭隔一條河扔隔壁村去。就是憑著這一把子力氣和家里的幾畝薄田,外公養大了舅舅,養大了媽媽。我們這些后輩們很不理解外公當時的決定,外公性子硬,只是簡單陳述了一個事實:“家里五個小的了,不回來種田就餓死人了。”
這確鑿是過命交情!我能夠體會到這句話中蘊藏著的艱難心酸與驚心動魄,但現在更能讓我陷入思考的,卻是外公以及趙支書熊姐夫阿麗姐們,他們對土地的那種不容辯駁的信任:如同孩子把熟睡交給肩膀,大地將天亮交給日出,在無數個種下去、長出來的`輪回中,他們跟土地建立了一種無條件的信任。土地永遠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也是他們最后的依靠。
這才是農村!只有農民和土地血肉相連,農民依托著土地,土地滋養著農民,這樣的農村,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農村。而一旦農民離開了土地,農村就蛻變了,或者說就墮落了。有人曾經這樣來形容新一代的農民們:讀書不成,十年靠膽大,十年靠賣力;末了膽寒了、力竭了,才想起家里那塊地......“膽大”自然是期望找到成功的捷徑,“賣力”就是四處挫折之后終于沉下心來,將自己的力量直接交換成所需價值,當然其中是不包括“賣力種地”在內的。于是,土地成了最末的、養老的選擇。“當農民不再相信土地”,這是一個怎樣的、令人傷痛的猜想。詩人用“荒蕪是農村的傷痕”這樣的詩句來尋求關注的眼睛,但浮躁的時代,冷漠的心靈,令憂傷如同荒草蔓延——我們需要開始思考怎樣去重建和做強這種信任關系。
前段時間偶然的機會去了相鄰湘江鄉的香草園,經過峽谷村道的時候,我看見道路兩側山坡上有一大片灰白色的植物,在滿是蔥綠的峽谷中特別顯眼,一問才知道是村民們種的厚樸。湘江鄉的鄉長介紹說:“這幾年厚樸價錢都不好,大家都沒怎么去采收,幾次說要砍掉,都是我們霸著不讓,說不定哪一年就看漲了,就當是綠色銀行吧。”
還有一次我返回大錫搭上了順風車,同車前往的竟然是省農科院的技術員——一個帶著眼鏡,滿臉憨厚的年輕人。他說已經在大錫駐了好一陣子了,栗木村那一大片甜玉米就是他在跟著,而且這只是第一步試種,以后還會陸續種很多新品種的果蔬,包括幾個市場上還沒有的品種。
每次聽到這樣的事情我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欣喜,這也正是我鐘情于像大錫鄉這樣的農村原因之所在。經歷過市場大潮的沖刷后,這里的人民依然在相信著土地,思考著土地,深愛著土地。
【相信土地經典散文】相關文章:
7.相信愛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