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遙遠的絕響讀后感作文
不是所有的風流,都顯得壯麗而又難以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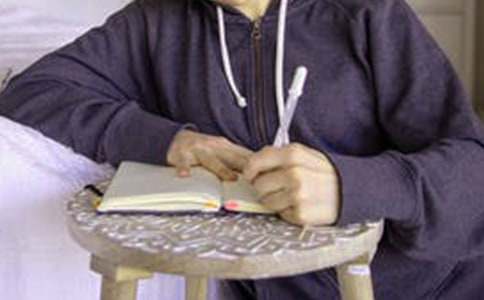
稱此獨為“魏晉人物晚唐詩”,絕不為過。
魏晉之風流、魏晉的灑脫與不羈,魏晉的處處透著鋃鐺之氣的“瀟灑”,之所以獨特于現世,或許是因為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說的,它誕生于“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
先是阮籍,他那種難以掩藏的文化感、歷史感,在魏晉這個紛亂的時代與無數的鮮血與頭顱碰撞、融合之后,超脫出一個更有標志性的灑脫的形象。“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當他駕著木車悠閑游蕩,在絕路前眼眶噴涌而出熱淚的時候,那必然不是悲哀于無路可走。那是一種錯雜而渾厚的情感,是一種找尋,是只哭給自己聽的來自心底對現實對生活最為真實的嘶吼。他的狂放、他的不拘禮法,至今都難以被人接受,可何嘗不能試著去效仿他在窮途時的大哭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真實地面對并釋放自己的心思,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在末路之前長嘆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我們不懂他究竟此言何意,但我們懂他的充滿寂寞感的豪情——那蘊藏在面向天地之間一聲震顫萬物的長“嘯”中的厚味。他不想做英雄,因而他只嘆英雄,嘆這紛紛亂世、豎子稱王。他已將世事看得透徹而深刻,因而他只要由著心去表達一個最真實的自己。我們學不來,因而只能仰視于他的灑脫,那種不滿足于世俗的追求乃至到了戲弄的程度的灑脫。我們,最多也只能活得瀟瀟灑灑罷了。
再是嵇康——對于余秋雨先生將他稱為“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可愛人物”的說法,無可爭辯,他的個人形象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比阮籍高出許多。他的瀟灑,甚至近乎漠視一切。他選擇了隱居,像世世代代眾多文哲圣賢一樣過著自己不受打攪的生活,但他又不與那些深居山林的棄世者等同——他竟略顯荒唐地在洛陽城外叮叮當當地打鐵。他不在乎塵世的熱鬧與繁雜,他甚至對此感到鄙棄,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真真正正所想要的,那永遠的安寧與滿足。他堅守著自己最不可侵犯的界限,一條已近乎到略帶傲慢的界限——但那不是傲慢。他的風流灑脫已將他隔絕在一個常人無法觸及的安寧而和諧的圈子里了,因而他能看到旁人是何等的嘔啞嘲哳。他會寫一臉的嘲諷與不屑,卻絕不會被那些無用的音響攪亂了心思。當他最終淡然地坐到刑臺上將一曲就此失傳的《廣陵散》彈畢從容赴死的時候,歷史這一端的我們,也被震撼了。這是何等的風流,何等的淡泊萬物?他的風流與超脫已在他身首異處的前一刻,毫無保留地彌散進歷史的長河之中。
可嘆的是,阮籍窮途的悲鳴長嘯,嵇康赴死的一曲廣陵,竟會成為歷史的絕響。
抑或說,他們那種難以復制的風流,也成了轉瞬即逝的一縷青煙,只存在了他們的那個時代,那短短魏晉之中又更顯渺小的那一段歷史之中。連他們血肉中剝離出來的后代,也完全不曾流淌一點點風流的血液,忠心耿耿地終命在官場之中。
我不知該如何悲于這已逝的風流。
轉視現今,當風流被冠以貶低的意思的時候,又一批已在中國的時間軸上銷聲匿跡的“風流”者烏泱泱地重現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不諳世事,放蕩形骸,趾高氣昂地從人群中走過——他們是“風流”了,他們甚至已經超出了“風流”所能包納的范疇而到了狂妄而放縱的地步。他們自以為已經達到那些“冥頑的古人”苦苦追尋一輩子卻也只能在日薄西山的歲月里短暫享受的那種獨立于浮世萬物的境界。他們以為那樣高傲地俯視一切、鄙視一切、將塵世污穢的萬物看得一文不值的時候,他們可以孤高地活。但他們可曾知道,他們這樣的流里流氣早已將“風流”二字抹得烏黑烏黑。他們也許可以“孤高”地行走在這個社會,但重點必然會是落在那無情的“孤”字上,他們也將必然成為這個他們眼中“俗不可耐”的世界上最終腐朽在這“俗”的泥沼中最另類的極端。
還有誰記得那個風流的年代,那些風流的人物,那份真正的意義上難以企及的風流呢?
當我們向往著“詩意地棲居”的時候,不要忘了還可以追求“風流地生活”。風流,是一個時代的財富、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而它更能是一個人真真正正作為有思想有自我的個體存在過的體現。
【遙遠的絕響讀后感作文】相關文章:
遙遠的眼神作文10-27
遙遠的眼神作文12-09
遙遠的目光作文12-09
遙遠的夢作文03-11
遙遠的故鄉01-18
在那遙遠遙遠的遠方現代詩詞12-09
原來并不遙遠作文03-02
彼岸并不遙遠作文02-02
最遙遠的距離作文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