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的散文隨筆
小城的散文隨筆1
我是在一個小城出生并長大的,生病前,我從未出過這座小城。不過它也不算是偏遠,但是由于依山而建,臨水而居的地理特征,這座小城總是有著它自己的生活節奏,城里的人不多也不少,有熱鬧,也不缺靜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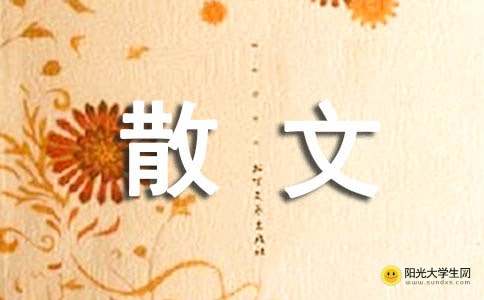
我的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在這座小城度過的。高中是在城區,可謂是“大隱隱于市”吧!學校竟出奇的不受外界干擾,就這樣,一撥又一撥的學子懷揣希望來到這兒,又帶著夢想從這兒出去。
不管天氣好壞,校門口的各種小吃攤在那兒雷打不動的擺著,攤主熱情的招呼聲、笑聲也讓這個小城經年已久的書香寶地多了幾分屬于凡世特有的氣息與煙火。賣燙皮的阿姨整天笑呵呵的,手腳麻利,在她的攤位上你不需耗費太多時間,烤紅薯的爺爺總會給你裝上那么大半口袋香噴噴的五香花生回去。
江河畔的水似乎一直都那么淺,一點都顯示不出作為湘江支流的氣勢來,但那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它的鐘愛,春天,我們相約在河畔踏青,夏天,我們戲水玩樂,秋天,兩岸的橘子成了我們的囊中之物,冬天,迎著暖陽,和摯友一起閑逛也別有一番樂趣。河一直都是那條河,但我們的趣味好似總也沒完似的。
說完了水,也該提提這山了,這座山我每年都要去爬上那么幾回,在我看來,用“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來形容它也是可以的,雖說沒有“霜葉紅于二月花”盛景,但每年春天一到,映山紅的盛放也不遜色多少。登上山頂,就可俯瞰全城,自生一番豪氣。山林深處隱約幾處廟宇道觀,香火四季昌盛,更為這座山平添幾分神秘和肅穆之氣。于我而言,每次上山,多半是要來拜上一拜的,無關乎迷信,為個心安念想罷了。
上了大學,離這座城也愈發遠了,逢上假期,也有數不清的事勞累身心,讓人脫不開身來,似乎再也沒有從前那般的閑情逸致來看看這座城。時間慢慢地走著,小城或許也有了些許的變化,但我仍想著我心中的那一座城,回味著那座山,那條河,還有,那已漸漸逝去的的時光······
小城的散文隨筆2
我住的小城位于中條山下,鹽湖湖畔,被農村包圍著,春天也來得特別早。
小城的公園里,有一座湖泊,很大很大,我前一天見它的時候冰凌還凍得很厚很厚,第二天見它時靠岸邊的冰凌就消了不少,第三天靠岸邊的地方就消了一圈水帶,再見它時水帶就越來越寬,由岸邊向中心迅速擴散,不幾天就被暖陽徹底融化了,整個湖面全部解凍,綠融融的一湖水,被微風一吹,就掀起一層層波瀾。有人向湖中投放石子,落水處就迅速向四周掀起一圈圈漣漪,剎是好看。
“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是真的。鴨兒們搖著肥大的屁股撲通撲通地跳下水,仰著頭“嘎嘎”地歡叫著,身后蕩起一條條優美的波紋。
岸邊的迎春花,也萌動了:骨朵兒胖長胖長的,披著紅色外套,在那里招搖過市,有的已經綻放,黃橙橙的小花兒,讓人目不斜視。開始是一兩朵,此后就一枝枝,一簇簇,一叢叢,搖頭晃腦地向人們報告著春天來臨的信息……
柳樹也蘇醒了,孕育著一個個小苞,在微微泛出青色的枝干上吐出新芽,柔軟的枝條垂下來舒展著身子,在春風的吹動下靈動起來,或東,或西,或左,或右,微笑著翩翩起舞,起舞中我用數碼照相機拍下了她的容顏,起名叫“春風楊柳萬千條”。
樹木之間的空地上拱出了一棵棵小草,黃黃的土地上朦朦朧朧的有了一點綠色,再去時就成了一片片嫩綠色的草地,爾后嫩綠色又漸漸變成了翠綠,墨綠,就像潑綠的水彩畫一樣,儼然一幅江南春色圖。
花兒也夢醒了,苞兒由小而大,含苞待放,一枝枝,一樹樹,可以用 “數點梅花天地春“來形容,雖然還未開放,卻紅苞滿樹,已構成一幅“含苞待放的春梅園”。不幾天,梅園里便繁花似錦,萬紫千紅,映紅了多半邊天。桃花也開了,白的,粉的,盛開怒放、爭奇斗艷。叫不上名字的小黃花,沒有葉子,屬于“先花出葉”的那一類,一簇簇,一叢叢,一溜溜,蹲在路邊,鋪天蓋地,繪成了一幅幅耀眼的“黃色彩帶”,真真切切的一道靚麗風景,我漫步其中,但見紅花、綠樹、山水、翠柏,濃蔭滴翠,姹紫嫣紅,湖光瀲滟,山色天成……讓人既品味出小中見長、步移景異的傳統特色,又感受到現代園林熱情奔放、清新自然的時代氣息,令人感慨萬千,流連忘返。
樹木中,綠帶中,空地上,時有野菜出現,如山菠菜,裸里頭,白蒿,灰條,蒲公英等等也趕趟兒拱出地面,撒了歡地瘋長起來,游客一見就蹲下來揪拔,回到家中,再搽搽,洗洗,綽綽,調調,便是一碟美味。
適逢為養母立碑,我攜全家大小回到農村,剛好“引黃渠”里的黃河水下來了,只見鄉村父老們搭埝的搭埝,修渠的修渠,平地的平地,澆水的澆水,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所有的桃樹地,蘋果地,棗樹地,小麥地,棉花地,都喝足了“黃”水,夢想著秋季的豐收,于是,便催生出一個個嶄新的、美麗的憧憬和希望,催促著人們辛勤耕耘的腳步……不言而喻,這又是一幅美輪美奐的“春耕圖”。
說話間,又下了春雨,“春雨貴如油”,我站在淅淅瀝瀝的雨中享受著春雨的滋味,企盼著春雨的收獲……這時,家里又忽然飛來幾只燕子,扒在上房的屋檐下忙碌地筑巢,孫女們見了高興地喊著:“爺爺,爺爺,燕子回來了!燕子回來了!”
燕子回來了,春天也來了,明媚的陽光下,人們甩開膀子在科學地大干,一個正在春澆的年輕人說:“一年之計在于春,只要緊緊抓住春天,扎扎實實地大干實干巧干,才能有大的收獲,才能實現我們的全面小康夢。”說著話時,我看到青山、白云、藍天倒映在澆過水的水畦中,映出了一個五彩繽紛的斑斕夢!
小城的散文隨筆3
十多年前,在小城的街角,常師傅就在這里修鞋。小城人有戀舊情結,我也是。一雙穿了兩年的運動鞋開線了,街上一溜兒排開有四五個修鞋攤,我來到了常師傅的攤位跟前。
“好鞋,頭層牛皮,厚實,丟了實在可惜。”老常說著,就把氈布鋪在膝蓋上,開始上手干活。他一邊做活,一邊和我嘮起來。原來,他是從山旮旯里出來謀生的。他告訴我,他有慢性病,也干不了重活,只好干點輕省活。他說,他修鞋跟別人不同,別人用硬線,活好做,但是頭結不死,容易開線。他用尼龍軟線,活不好做,但是不會開線。如果能縫線,決不用膠粘。用膠粘只能頂一時,不結實。
常師傅將鉤針伸到鞋里,鉤,拉,穿,結,細致專注,不一會兒,鞋就修得嚴絲合縫。我問多少錢,老常擺擺手:“活小,不要錢。”我執意要給,他推開我的手,說:“下次下次。”當下就又接了另一個客戶的皮包,開始仔細端詳,斟酌修復的方法。
自此,我就成了老常的客戶。老常蹲在街角,冬天,西北風把他皴皺的手扯出幾條血口子。夏天,陽光給他裸露的肌膚印上一個背心的圖案。一個修鞋匠,為小城的人留住了懷舊情懷,留住了一節節舊光陰。
世事嬗變,時代把修鞋這一門手藝逼到了邊緣,大多修鞋藝人湮沒在歲月之中,或者說,是生存需要讓他們重新選擇了職業。在小城拆遷重建的過程中,老常就像一尊雕塑,成為這個小城永恒的風景。
最近,微信朋友圈里的一條消息稱, 老常師傅新開了一個修鞋店,開展修鞋、擦鞋、洗鞋和掉漿補色、破損修復、大鞋變小、小鞋放大等業務。我決計去看看,很長時間沒有去修過鞋了。
在一家超市對面,果然看到了常師傅的店。那是一個小閣屋,有一人高,4平方米左右,墻上掛滿了各樣的修補用品。常師傅坐在那里,跟前擺著一臺锃亮的機器。他的身邊,圍著幾個老年客戶。與以前不同的是,常師傅鼻梁上架了一副老花鏡,他在專注地縫著一只經年的黑色皮包,不時抬眼和顧客交流著。他一臉沉靜,是那種飽經歲月滄桑的沉靜。
“常師傅,該歇手了,如今政策這么好,吃個低保,加上農村養老金,錢夠花了,還出來做啥活?!”我走上前去打招呼。常師傅認出了我,他淡淡地笑笑說:“我這長秧子病,10年了也不耽誤干活,你看我現在還能折騰。咱從來不要國家照顧,也不去爭低保,還有比我更困難的人哩!”
丹桂之香飄來。因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勞動者,我覺得小城多了一份溫情與美好。
小城的散文隨筆4
我的家鄉是廬山西海湖畔的一座山水小城。初夏的黃昏美麗而綿長,直到七、八點鐘,日光才逐漸黯淡消失,抖落了一身喧囂的小城,落日、晚霞和涼風以大自然的筆墨裝扮著她的天生麗質和迷人的神韻。
在小城待得久了,越發覺得這座小城的好,卻說不清好在哪里,只覺得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親近可人。我家前面的不遠處便是沙田河,河的兩岸是小城最美的濕地公園和文化生態公園。這條小河就像它的名字一樣質樸安祥,安祥得讓我常常感覺不到它的`流淌,它婉若一條閃動著熠熠微光的玉帶,由南向北,穿城而過注入廬山西海。
走在沙田河畔,微涼的晚風,攜帶著清新的草木氣息,習習吹來,把一天的暑氣與疲憊盡數吹散。舉目望去,臨水而建的“八音樓”,依托以“中國古代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制作材料對樂器的八音分類”而命名的“八音公園”,雄踞于城市的西北城中。白天人們登上高樓,小城的新區風貌,便可盡收眼底;到了黃昏的時候,在清新悠揚的音樂聲中,“八音樓”亮起燈光,彩燈璀璨明亮,遠遠望去,猶如一座晶瑩剔透的水晶琉璃塔,點靚了城市的一角夜空。
清翠綿延的七里群山,猶如一道綠色的天然屏障,隔湖守護在小城的北面。它使我想起少年時曾和小伙伴們上山砍柴、拔筍、摘野果的情景,那時半山路邊一株巨大的老茍樹下,曾住著一對面慈目善的老夫妻,免費向過路歇腳的客人提供用木茶桶裝著的山茶果涼茶。而我假日里砍柴經常路過,沒少享受這清暑解乏的山茶果涼茶,時至今日,對山茶果涼茶的爽口清香都記憶猶新。如今路邊的野花、山果,在黃昏里搖曳生姿,提醒著我,原來花果飄香并非幻覺。
沙田河邊的小徑,最是清幽的所在。這里草木蔥蘢,高低錯落,疊疊層層,高的有楊柳和香樟,矮的有黃揚、山竹、夾竹桃,還有各種綠草及權木,只是大多我都不識得名字。初夏的垂柳,已出落得婷婷玉立,一條條柔軟的枝條,長長短短地垂下來,輕輕地拂過水面,盈盈地撩動著人們的情思。雖已是人間六月,但夏日里開的花,依然是臨水照影、爭奇斗艷,不論是紅的似火,還是黃的如綢,都一樣吸引著行人的目光。石榴花正紅,夾竹桃正俏,還有許多叫不上名的花兒在暮色中悄然開落,把整個黃昏點染得異常美麗而又略顯得有些惆悵,這些花兒是在惋惜逝去的春風,還是傷感這稍縱既逝的黃昏之美?
穿過長墅大橋,來到河的對面,這里街道寬闊、綠樹成蔭,新的學校、幼兒院、劇院、公園、商廈、展覽館、居民新樓、行政新區、西海燕碼頭和旅游中心……,拔地而起、錯縱林立,是小城人自喻為西海明珠的沙田新區。長墅大橋邊的文化生態公園和濕地公園一水相連,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線,生態公園里幾乎匯聚了本地所有的花木品種,在各種奇花異草之間,或用文字,或用雕塑,或以圖片,講述著小城人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讓人欣賞美景的同時,又能感受到這座小城濃濃的文化底蘊。
這時行人甚少,景色更添幾分幽靜,一條曲曲折折的小橋、長廊,浮在這煙波蕩漾之上,盡頭處,恰到好處地立著一座精致小巧的拱橋。人們極貪戀這里帶著水氣、輕柔的河風,傍晚散步時,往往便要繞到此處,水面上有細小的浮萍,還有新種的荷花、水草。拱橋過去,便是一條幽深的林蔭小路,平整的路面是由大理石鋪成的,走在上面,疾步無聲,帶著幾分私密和親切,令人愉悅。
小路盡頭的廊橋是木制結構,古色古香,外圍可憑欄望水,內廊可擇椅小坐。我們經過廊橋時,常見有三兩游人,散坐閑談;也有年輕人,獨自玩著手機,在此貪風納涼,抑或許,他(她)是在等待自己的戀人吧?待到月上柳梢時,在嫵媚柔情的飄香荷塘畔,一對對青年情侶娉娉婷婷如約而至,牽手漫步。
暮色漸濃,小徑上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人們都喜歡來這里納凉散步,多半因為這里水平如鏡、環境優雅。沙田河兩岸當是小城的小西湖了,環湖皆是蔭蔭翠色,湖上亭臺小橋,錯落雅致。暮色四合之時,各種燈光,與湖邊的亭臺樓閣軒榭廊交相輝映,倒映水中,猶如滿天星斗撒落在清澈的河面上,分外迷離和夢幻。"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豈有幾回聞"傳說中的瓊臺玉宇,蓬來瑤閣,想來亦不過如此吧?坐在湖邊的長廊里,聽歌看景,真是清歌曼妙,好風好水,別有一番心境。
散步時,路上常會遇到熟人,在隔樓如隔山的城市中,許久不見的熟人和朋友,在黃昏中不期而遇,的確是件美好的事情。迎面相逢,人們的臉上都寫著意外和欣喜,正是閑暇時候,不免要站在路旁,就著這一湖山水,幾縷閑情,聊上一會兒,說上一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消磨盡這初夏黃昏里的寸寸光陰。
直到月上柳梢,聽著小河里蛙兒們的彈唱,帶著湖邊的涼爽,踩著悠閑斑駁的樹影,小城的黃昏才帶著最后的幾分不舍,意猶未盡地悄然離去。
小城的散文隨筆5
談起泮池,讓人聯想起小城的必定有著悠久的文化淵源。曾聽說泮池是古狀元入學時走得橋,過泮池上的橋,方能入學。泮池還在,讀書人敬仰地孔廟也搬上了佛家凈地,小的只有一間小平房,僅能容下嬌小的孔子塑像,以供學子祭拜,庇佑考試能出好成績。小城是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你看泮池后的百米不足的小巷還名之文廟街。
可惜小城的泮池的遺留似乎和文化無關,但是和明建文帝有關,傳說建文帝曾再小城獅子山削發為僧期間,被囚于泮池上的屋子,那時正值夏夜,蚊子嗡嗡聲響不停,橫沖直撞,就像一個個流氓痞匪在趾高氣昂欺凌弱小為榮,唱著所謂勝利凱歌,加之池內青蛙也不甘示弱的呱呱叫個不停,對飛舞的蚊蟲予以鄙意,要不是你有翅膀飛得高,早就是是我的口中之物了。炎炎夏夜,口干舌燥,蚊蟲和青蛙還在爭吵,讓淤積心中的憤怒一下爆發,但還是無奈的發出請求,哀求蚊子和青蛙不高歌和爭吵,蚊子也不要用那尖嘴不停地叮咬人。話說靈驗,哀求的話語剛畢,青蛙和蚊子啞巴了,蚊子收起尖尖的小嘴不咬人了。從此以后,泮池的夏夜人總是很多,老人、年輕人,時髦女郎、皮肉女人……
不知從何時起泮池多了一個塘字,聽著極不習慣。多好泮池似乎從文明的巔峰一下墜入了凡俗的深淵。曾幾時,只有狀元、讀書人才能走的泮池橋,才能游逛賞玩的泮池變得低調親民,才是容納大家的步伐。看著簡陋和破敗的遺留建筑,只有泮池中間呈兩層鍍金色黃瓦覆蓋小塔,還挺著斑駁陸離的軀體在矗立著,泮吃的圍欄倒了再修,修了再倒。想著當年的泮池該是小荷尖尖托著晶瑩的露珠,小魚自由地在荷間戲動,忽南忽北,隨風而起。那只蜻蜓何時靜靜的立于荷瓣上吮吸著著露地,一身書氣的文人在此苦讀書經。隨后的池里,荷花已歿,一尺黑褐色的臭水中也還有幾條小魚,吸引著些鶯歌燕舞的閑人、雜人前來嬉戲,路人唯恐避之不及。
曾何幾時,就連臭水也干枯了,什么也沒有。泮池雖還在,但文氣、人氣已消逝了。
小城的散文隨筆6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么,浙江的臨安就在天堂的旁邊。
臨安這地名給人的印象更像是一個客棧,或者驛站,當然是通向天堂的客棧。在那進而距天堂一步之遙,再回頭俯瞰人寰,那種自得與從容,就使人生變得十分瀟灑了。
臨安是旅游名勝地,對于旅人來說這地名再貼切不過了。
在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這些引人注目的明星背后,臨安偏居一隅,不顯山不露水,只能算得上是小家碧玉,玉樹臨風,獨善其身。臨安是這些大都市的后花園,是紅塵滾滾中人們心靈的避難所。臨安山清水秀,人杰地靈,民風淳樸。身居大都市的人到了這里才知道“滿目青山覺筍香”是什么感覺。臨安人的生活舒適,安靜恬淡,悠哉游哉。這么說有點廣告詞的嫌疑,可事實確實如此。
到過臨安的人都知道,每到周末或者節假日,臨安的大小賓館客滿為患,各種車輛絡繹不絕,各色人等接踵而至。他們衣著光鮮,感覺良好,帶著大都市人的優越感,那份暫時逃離了名利束縛的輕松,那份臨時的放松、瀟灑與滿足,使他們神情自若,左顧右盼,煞有介事,呼朋喚友,指點江山,放浪形骸。他們飽覽了青山綠水,品嘗了野菜鮮筍,舔凈了心靈的傷口,縫補好了破碎的心,帶著藍天白云般的好心情又回到名利場中去了。
旅途如此,人生莫不如是。人生就是一次旅途,當然是單程的,人在世上所求的大概也就是臨時的安定,生命以后才是永恒。
臨安這地名透著更多的哲學意味和人生真諦,還有一點悲劇氣息,似乎將人生說透了。臨安就是人生的客棧,誰來到人世間不是臨時的呢?無論榮華富貴,窮困潦倒,飛黃騰達,艱難困苦,不都是臨時的嗎?不都如過眼云煙嗎?人生是臨時的,這道理誰都明白,人們企求的是臨時而安定。人們在名利場中拼博廝殺,往往忘記了安定,變得浮躁功利,爭強斗狠,貪得無厭,弄得形態丑陋,俗不可耐。于是,他們需要到臨安去安安心,定定性,“身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所以就來了,所以又來了。
臨安給人心靈留下的印象是傷感的,惆悵的,留戀的,向往的,也是純凈的。給這地方取名字的人無疑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滲透了人生。
臨安距杭州不到50公里,坐汽車半個小時就到。這點路程實在是小意思。在臨安當一介良民,舒舒服服、安安穩穩地過完人間的日子,待時辰一到,一步就可以跨入天堂,方便極了。
小城的散文隨筆7
北方已經飛舞雪花,而南方的枝頭,卻仍有花兒正艷。
在這座美麗的小城,能登上榜單的花朵,有朱槿、三角梅、也有秋棉。朱槿的鮮,三角梅的熱烈,秋棉的淡雅算是這個季節里大自然特別的眷戀,它們出沒的地方總仿佛一幅幅被精挑細選的油畫陳放在人世間,它們構成城市個性的名片,并與世界和諧鑲嵌,或匯成湖,或堆成山,或綿延成道路,讓城市長出無可挑剔的精致與莊嚴,流連著仿若朝花夕拾的變遷。
美麗的花與青翠的樹在此蜿蜒,一半因為積淀,一半因為心愿。亞熱帶氣候的綿延加上靠近海邊,冰天雪地顯得特別遙遠,而人們在道旁精心栽種的這些光鮮,在沐浴了靠近赤道的陽光之后,便擁有了不老的容顏,它們經歷過春天,也經歷過秋天,卻始終葆有青春無敵的耀眼。
盡管也有梧桐落葉隨風,但作為秋的祭奠,更多的時間,生命把周邊度化成豐年,它們努力舒張,盡情吐露芬芳,不拒絕幻滅和流浪,不拒絕塵煙和迷茫,渾沌或純粹的激昂,始終洋溢著古道熱腸。
在人們的記憶中,爭奇斗艷很有可能會將流年或煙雨驅離,但在這方土地,人們只要睜開雙眼,花開花謝總能提前要約,滿足您的期待或令您無比懷念。
小小的一座城,河岸邊的草青了一年又一年,路邊的樹果實掛了一遍又一遍,人世間來來去去的云煙仿佛卻始終停留在原點,它們不知有無從前,也不知有無明天,以最合適的距離遠離滄桑和巨變。
順著路沿,人們很容易看到天色深深淺淺,蔥蘢忽隱忽現,在隱約的樓宇中間,墨綠或火紅串出許多意外的驚艷,有香飄千年,也有幸福滿園。
蜂蝶生活在桃花源,就像人們安樂在伊甸園。它們采集、醞釀,也收獲和釋放。它們美麗的翅膀經常出現在視線的周邊,帶著流動的寫意,也帶著輝光和理想,熾熱如這片土地上生長的各種希望。
江水如帶,款款繞城。盡管流水并不是這個季節的特長,但淙淙顯然也是一種向往,它們從來時的鋪張,到去時的明亮,一直在喻示喜悅和成長。
陽光同樣明亮,它們的飛揚有很貼心的磁場,它們在行進中留下安詳,也留下溫暖的榜樣,有歲月那么豪放,有情懷那么明朗。
這些日子,我一直在猜測,這究竟是誰的故鄉?
不見晝短夜長,紅花綠葉滿庭芳,大道兩旁,天是自由的方向,橋和路直指南山,和風爽朗,儀態萬方的秋水像待嫁的新娘!
小城的散文隨筆8
一、小城的眼睛
我把青龍湖比做小城的眼睛是有原因的。
現在是秋天,水清云淡,流連轉動,開始它一年中的思緒和凝視。有一次雨天我獨自去,走進它澄澈的眼眸,在欄桿處融入天水一色里,我成為它虔誠的影像,安靜下來,看時光在眼前走走停停,一閃而過,我是它的瞳孔。
青龍湖有十二個年頭了,從子排到亥,繞過一圈的途路,古人謂一紀。起初它是田園,竭盡所能,費盡心思為一方百姓供奉四季莊稼,養活無數生靈。后來辟做窯場,沙土適中,燒出的紅磚青瓦方正、結實,敲敲清靈有聲,被運向城里,建設高樓,運往鄉下,翻蓋大屋,為它們做衣添衫,它問心無愧。無土可用的時候,它深深陷落下去,高大的煙囪指著虛無,雜木亂草叢生,閉著眼,看不清風塵和雪月。那時候我的一個朋友住在里面替他的舅舅照看窯場,我叫他“窯主”。他整天土頭灰臉,眼睛干澀,談女朋友的時間都沒有,他厭煩透了,什么時候是個完呢。
湖是一個叫王天順的人撐頭、在廢棄的窯場修建起來的,起名叫青龍湖。它的北面還有個廣闊渠,水源不斷地從北汝河引過來,分給青龍湖一部分,剩下的滋潤附近的土地。青龍湖亮汪汪的,空氣濕潤起來,春夏碧翠墨綠,秋冬清靜高遠,成為小城的眼睛。南來北往的鳥類路過此地,只低頭看了一眼,盤旋幾圈,俯沖下來,洗洗風塵,住下來,不走了。
那天我去的時候,雨索索下著,敲打小傘如叩問。野鶴這時候飛來,長時間站在淺灘處凝視水面,等待魚兒游過來,然后長長的啄閃電出擊,穩準狠。我們當地人叫它們“老等”,老等什么呢?等希望,等以后殷實、有魚的日子。小燕這時候快要上路了,出發前的日子,在湖面、亭臺長廊上方俯沖低飛,捕捉潮濕的蟲子,勤奮忙碌,積蓄能量,種罷麥,它們飛往南方。
笠帽閑裝折疊凳,雨飛風卷波橫。一位釣者坐在湖邊,不動聲色,悠閑甩線執桿。雨也許是青龍湖先前的水,重又回來,魚確是這湖里終生的魚。他釣的是心情,是過往的日子。一條長長的欄橋把湖一分為二,南面一只水鴨獨自抖翅搔首,喜樂玩水,很高興的樣子,釣魚人叫它“喜哥”。北面有三個水鴨舞蹈生風,那小點的也許是女兒,跟在后面,蕩漾自己的漣漪。
陰雨天也有它的明亮。甬道的兩旁是樹木,樹下鋪滿草的綠毯子,此時如果俯身打一個滾兒,渾身上下就會沾染綠色而詩意叢生吧。路兩旁樹的枝椏牽起手來,連在一起,陰涼幽靜,下面灑滿黃燦燦的落葉,滿眼憧憬,醉意四方,而前方就是光亮,仿佛明天蹲在那兒。我走過去,一下子跌進開闊里。
又一個十二年開始。我的那位窯主朋友在湖西買了套景觀房,站在四樓,他時常看青龍湖,看失去的青春,青龍湖也看他,不多說一句客套的話,相互凝視,如彼此的初戀。而水霧里,湖面有四只水鴨在一起戲水,其樂融融,其中一只定是喜哥。從此,它是湖的主人。
二、小城邊緣的樹林
這片楊樹林在城南三里一個叫南大洼的地方,我叫它南大洼叢林。穿林而過的靜幽和意境里,我寫點詩情畫意的文字給它,跟它說說話,留下喜歡,帶回清新一片。早些年網絡博客漸興,我給自己起個筆名叫“城邊林”,他們說,多好的名字,你們那里樹多吧。不可否認,那是我見過的最多的樹,遠遠地栽種在四季的幽深里,像小城的眼睫毛,成為日子的屏障,遮擋自遠而近的風和雨。
我步行去,幾乎每天早上都要和它們打聲招呼。在晨霧里,這些沉思一夜的樹木激靈一下醒來,樹梢動了一下,撓撓頭,所有的樹葉舒展開來,彌散著從土地里升騰起來的沖動。水珠“嘀嗒”落下,砸在另一片葉子上,帶動眾多的珠兒向下跳,下面是螞蟻的家,打斷它們一天的行程。地上許多柔嫩的藤蔓植物,起初匍匐在地上,趁著工人放下鋤頭的間隙悄悄爬上樹根,看看沒人阻止就攀沿上去,紫色的、紅色的碎花點綴其間,像樹的裙裝。
天旱的時候,林子里幾口井會同時歌唱,把水源傳遞給每一棵樹木。水渠是我小時候見到的那種,清凌凌的水流過干凈的、細細的鵝卵石沙底,葉子浮在上面,去往另一個地方。失足落水的蟋蟀常有,它的身下形成一個水膜,輕輕地浮在上面,有時是兩個,在水渠岔口處分手,飄呀飄,抵達樹木的根部,匆匆上岸,結束旅行。也許有一天兩只蟋蟀在一顆狗尾巴草上相遇,彼此看上一眼,碰了碰觸角,就認出河流上那次難忘的漂流。
樹林里最忙碌的是喜鵲。它們每天按時巡視屬于自己的領地,給巢里的雛鳥帶回點心和愛意,唧唧喳喳嘮叨不停。有一次,我聽見一只知了尖利的嘶鳴自遠而近飄過來,抬頭一看,分明是一直漂亮干凈的喜鵲在飛,落在一個碩大的鳥巢上,原來是喜鵲母親給自己的孩子帶回一個會叫的玩具。忙碌完畢,喜鵲們開始一天的歌唱,在祖輩傳下的村莊生活,它們的聲音低沉而深邃,掠過土地,驚起草動,唱著千百年不變的歌謠。
一條青磚鋪就的小甬道通向林子深處,我輕聲過去,貼近樹林的心,風一遍遍撫平樹上的傷痕。這是一塊籃球場大小水泥地,整潔、靜幽,像樹林寬敞的舞臺。這里曾是一座房子,上層建筑消隱于流年,根基和記憶留下。可以想象出一個人住在這里,擔水劈柴,養牛放馬,滿眼清澈,內心裝滿綠韻,該是詩鄉里一間明亮多彩的小屋。我給小城里的一位詩人說,我們可以在這里朗誦詩歌,唱歌,跳舞,在樹木的涌動里揮灑多年積攢下來的聲音和姿態,或激揚,或低吟,或靜默,林濤做和聲,流水記錄下今生的音符。秋天,雨季來了,愿望成為遠望,放在歲月的鳥巢,等待飛翔。
我有許多天不曾過去了。雨季前,樹林來過幾撥伐木人,一陣陣刺耳的電鋸聲過后,一棵棵樹木轟然倒下,驚起落定的塵埃,露出天空,喜鵲失去房舍,而城市已經在望。為什么容不下這片綠意,留下這片樹林,留下我們這座小城的眼睫毛,它們看上去是多么美好,一旦沒有了,除了凌亂的街道,我們還有什么可以值得保存。
現在是深夜,我裹緊衣服。南大洼叢林,你一定感受到了雨季的涼。
三、小城再現饸饹床
家中停電,酷熱難耐,出去解決午飯問題。不想大半個縣城也是停電,一條街快走到頭,終于看見一面館門前人流涌動,各種車輛橫七豎八停在兩旁。遂大喜,抬眼一看,門匾之上赫然寫著“正宗手工饸饹面”。醇香和熱浪迎面襲來,但見大堂里男女老幼圍桌而坐,執筷挑面,旁若無物。一人齜牙咧嘴端著大碗邊走邊喊:“燒住了、燒住了”,人群立馬閃開一條空隙,迅即又合攏。
沒有電,咋用機器軋饸饹面?店家聰明,人家把閣樓上一二十年沒用的饸饹床兒派上了用場,擦拭清洗,往大鍋上一跨,手揉的面團扔進漏子里,一個結實高大的人坐于壓桿之上,成泰山壓頂之勢,一起一坐,柔長的面條從底部的漏孔里緩緩出來,在滾水里一煮,然后大師傅拿著筷子手腕一挽,挑起渾圓勁道的面條,放肉、碎蔥爛芫荽,最后放紅油辣椒進去,一碗碗噴香的饸饹面制作出來,仿佛那個遠去的年代,也一碗碗端了回來。
外地人有所不知,這饸饹面存在已有上千年歷史,前人用牛角鉆孔,置面糊入內,以手按打,漏落進沸水鍋中煮成面條,故也叫河漏。怎么傳過來的,民間有許多說法,也許失真,但我以書載為準。明人張居正《昌黎先生文集輯補》一書“諫迎佛骨”中有韓愈的一段話:“元和年間,自蔡屠賊歸,途食郟河漏”,說的是公元818年的那個冬天,韓愈隨唐軍平叛“淮系之役”,唐軍行至郟縣城西吃了饸饹面。也就是說,饸饹面傳入郟縣至少有1200年的歷史。
這饸饹床兒在以前是店家的重要設備,生意越好,磨損、更換的也厲害。上世紀90年代,我們本地人開發、研制出電動“饸饹機”替代饸饹床兒,后來人也懶了,和面切肉切蔥也用上機器,省時省勁。但老輩子人吃起來,總覺得少種味道。經過改良的饸饹面,口感和勁道似乎差了些,四十歲以上的人一吃便能品味出來,年輕一些的、特別是小孩子,沒啥感覺。老人搖頭說,你是光吃羊肉沒見過羊。
我第一次吃饸饹,是剛上初中那會兒,進城參加縣里運動會,中午集體去一家饸饹店吃面。正是夏天,人聲鼎沸,開鍋一般,女的短裝,男的大都光著膀子,挑著面條吸吸溜溜往嘴里塞,旁邊一個制作火燒的爐子熱騰騰燒著,像冬天取暖的煤火,火肚里不停扔出火燒來。每個人碗里漂一層紅亮的辣椒油,再看壓面的師傅,也是光膀子坐在長長的壓桿上使勁蹲壓,不時用手朝身上摸一把汗甩出去。一個鄉下的孩子,真真被那恢宏的陣勢嚇倒。
后來我去外地上學,畢業上班,外地有了不少朋友,來到郟縣,無一例外地先讓他們品嘗正宗郟縣饸饹,吃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一個許昌的同學早年過來一次,似乎上癮,參加工作后隔一段時間就帶上家人朋友過來。起初找我,后來感覺不好意思打擾,坐車來了就獨自去吃,回去后再打電話給我,讓我很沒面子。也罷,厚德載物,一碗味美湯鮮的饸饹面讓一個外地人不辭遠途來往郟縣,也算是我這個本地人的榮光。
郟縣人吃饸饹面已成為生活習慣,有人一天三餐也不嫌少。頭天晚上酒喝高了,喝一碗;中午不做飯急著有事,到饸饹店立等可取;酒店請客吃酒到最后,不上一小碗饸饹面不算吃飯;吃饸饹面不吃上一塊焦黃的火燒不帶勁,像山東人吃饃就大蔥一樣。不管身份高低貧賤,來了就自己端碗拿筷、加辣椒油要面湯,吃喝完抹嘴走人,一撥一撥食客來去自由,享受的是淳樸之風。從外地回來的游子,一踏上家鄉的土地,下了車,風塵未去,先去饸饹面館,抓一塊火燒,急急擠進人群,端一碗滿當當的饸饹出來,坐定,來不及攪動,咳嗽一聲,只片刻,看見碗底。
也許一次偶然的停電,讓傳統饸饹面重又回來,喚起人早年的情思,拖拽出小城久遠的回憶,是另一種無處再尋的佐料。
小城的散文隨筆9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來的比較晚,南方小城初經春雨,潮濕中帶著點黏人的泥土氣息。
巷口的糊湯店異常火爆,到處都散發著濃濃的年味,華捧著有點燙的碗,輕輕的吹著,然后緩緩地將糊湯遞給面前的芳。“我不餓,你先吃吧!”芳把碗推給了華。“不行,你先吃,你還要趕火車呢。”華又把碗捧給芳。“玩夠了沒有啊,這碗放哪呢?”老板又端過來一碗,不耐煩的瞧著二人。
“給我,給我……”華尷尬的接住,偷偷瞥了一眼芳,芳耳朵紅紅的低著頭。
“明兒我就去單位打申請報告,組織上不一定能批下來,你在等我幾個月!”芳邊吃邊說。
“多大點事,都等你一年多了,不差這幾個月,等過完年我把俺家那院子捯拾捯拾,給你騰個地方出來,娘說了,就怕你住不慣。”華呵呵的笑著。
芳突然抬起頭來正好和華的眼睛對上,“如果調動批文下不來,咱們的事就得再緩緩了”
華突然激動的握住芳的手,“別瞎說,實在不行我就過去。”
站臺上的火車已經駛離,華依然追著跑出了半里路,他看到淚流滿面的芳沖著他招手時,隱隱感覺到有些不安……
春去秋來,芳再也沒有踏足過這座南方小城,那一年父母將其關于屋內,苦口婆心勸說大學畢業的芳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婆家。
而華借著親戚的關系出海經商,這一別,十年匆匆而過。
當年的糊湯店已經不在,而故事依然在發生,南方小城變化飛速,改革開放的春天不僅帶來了富裕,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華。
又一年過去,當他們再度重逢與南方小城,各自發白的鬢角又在述說怎樣的情愫。
也許故事只是故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他愿不愿意說,或者有沒有合適的情境說,亦或是有沒有合適的對象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體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可。
過眼云煙,浮世塵華只不過是凡人背負的罪過,當雙手合十,學會放下,又有幾人能懂。可悲的不是死心不改,可憐的是回頭無岸啊……
二月南國春水柔,
一宿花落雨初收,
夢里少年吹簫伴,
一眸相望各自愁。
小城的散文隨筆10
望三秦煙火于云端,聽巴山夜雨于窗前。扼成渝之要津,聚沱江、涪江之清流。一江水,一座城,應韻成生。安居于岳,普州人世世代代躬耕于這片熱土。
――題記
一
故鄉的縣城,原來我認為它是很小。小的只容得下鄉音和那些靜默的粉墻黛瓦,亦或滴滴嗒嗒的雨聲,枝頭懶散的陽光,幾聲啾啾的鳥鳴,走街竄巷的叫賣聲、茶館里的說書聲。
但現今看來,它遠非我想象的樣子。三月煙柳蒞水,清影弄波。三兩枝桃花開在寂寞的竹籬外,它們并不在乎無人問津,也許時光會薰染成一紙桃箋,給遠方思念的人一封書信。石板路連著阡陌,曲折的岳陽河不聲不響地淌過城市裸露的身軀,摩挲著它的每一寸肌膚,然后奔向田野、遠方。鱗次櫛比的高樓在一片蓊蓊郁郁中失陷、沉醉不醒。
偶兒也聽到一些吳儂軟語、南腔北調,這些異鄉客大多是來普州作投資的商人。
“老板,來一碗傷心涼粉。”客多時隨便選一個旯旯角角一坐,吃得頭上冒煙,揮汗如雨。“這個麻辣真他娘霸道。”張口伸著舌頭,卻又欲罷不能,筷子還是不中自主的伸向了碗里。不言而喻,傷心涼粉最容易勾念起鄉愁,對于這些異鄉游子也會想到故土、母親。生活中的麻辣辛酸、人生五味自然會在一道美食中品出一二。
“老板,給我炒一份壇子肉,聽說這是你們普州的特色菜哦?”老板滿臉堆笑,這個咩不用說了,古代時沒有冰箱,突遇家中來人來客招待自然很不方便,那時趕集又遠。而巴蜀之地的百姓幾乎都會做壇子肉、油底肉,也方便儲存。家中來客,不失為一道好菜。
百姓過年殺了年豬,就把適合作壇子肉的留下,以備用,這樣就可吃上幾個月。由于蜀中天氣多陰雨潮濕,煙熏臘肉也放不了幾個月就長霉了,而壇子肉放在全封閉的壇子里,能儲藏的時間較長。入口化渣,肥而不膩,適臺搭配各種生鮮蔬菜,自然成了一道美味佳肴,故一直流傳至今。
做壇子肉說來還有些講究,一層羅卜絲咸菜,一層炸成金黃的肉墩,抹上五香粉入味,再放在蘿卜絲、豆角的壇子菜上。做咸菜的羅卜絲需曬干才行,否則壇子肉做出來是酸的。肉多余的油脂會被咸菜吸收了,肉有菜的清香,菜有肉的濃郁之味,相得益彭。吃起來肥而不膩,入口化渣,只要肉一入鍋,肉的芬芳素無形之中會被誘發出來,風一拂,遠遠能聞它的香味。
幾位搞房地產的老總聽店家如此一說,菜還未上桌,口水在喉嚨里早就響個不停了,敲著碗向老板催菜了。
盤龍黃鱔、涼拌米卷、春筍燉雞、烏魚三吃……說到普州的吃啷個(怎么)說得完。
二
吃好了,你也可就近到縣城周邊的圓覺洞、千佛寺、木門寺到處轉一轉。普州有中國石刻之鄉、佛雕之鄉之美譽,可與大足石刻媲美,石刻起于唐,興于宋,佛雕栩詡如生。故,普州之地香客甚是鼎盛,如見老者慈眉善目,少男少女眸子如清潭照影,兒童一臉陽光,你不必訝異,物寶天華之地,自受地域人文風情和古風薰陶。
若你累了,可在南山公園瘦詩亭小坐。這里曾是詩人賈島駐足之地,他也許聽著圓覺洞的鐘聲、木魚聲入迷,在此放下了所謂的功名,在一片片紫竹婆娑中看龍飛鳳舞。我不知,當時的他是否為大唐的國運祈禱,在圓覺洞雙手合十?他最終選擇了在這片土地安魂、靜守。
站在忠孝亭可見普州全貌,抗日戰爭時,很多人從這里走了,再沒回來。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有些人埋在了鴨綠江的那邊,僅一江之隔。我想,他們是為國而戰,是不想讓以美帝國主義的多國聯軍飲馬鴨綠江,讓國土再遭到別國的入侵。他們于國是忠的,對父母我不知是不是孝?如果是,我想是大孝吧!沒國哪有家?岳飛母親為岳飛背上刺字“精忠報國”,花木蘭替父從軍,穆桂英掛帥,他們誰又不是英雄楷模呢?
一夜春雨萬物新,新城燈光如虹,塔林星徽閃耀。老城一河柳絮護堤,幾多門市若壁掛珠簾,似透非透,令人浮想翩翻,店主是鶴顏的老者?還是玉樹臨風的少年?或是娉婷而立的女孩?
那一條長長的青石雨巷沒有回應,我仿佛看到了丁香一樣的姑娘,驚鴻一瞥,再不見油紙傘下的模樣。只見長滿苔蘚青磚的雨巷,影子悠長悠長,但我不知自己為什么這么寂寥、這么憂傷?
【小城的散文隨筆】相關文章:
3.小城初冬
4.小城之戀
5.小城的慢時光
6.小城故事作文
7.小城清商
8.煙雨小城散文